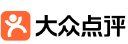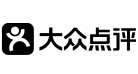Sham Tseng Goose (Huayuanxincun Branch)
AVG. COST
¥26
Recommended dishes
Ratings & Reviews
Good to Know
Free Wi-Fi
Parking
Delivery
Pet Friendly
Similar Places Nearby
Sham Tseng Goose (Guancheng Branch)
Jiaoge Friend Dongguan Roast Goose (Huayuanxincun Branch)
Rongji Dongguan Roast Goose (Fuyi Garden Unit Shop)
Lichee Chaixiankao Roast Goose
Houjie Roast Goose (Dongcheng Branch)
Weiji Roast Goose Laifen (Wenhua Garden Branch)